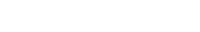寻找属于自己的语词,与时代连接
【编者按】
走过一年的风风雨雨 , 迈过一年的坎坎坷坷 , 时间即将掀开新的一页 。澎湃评论推出年终特别策划《让未来配得上现在》 , 记录和书写你我的2021 , 期待在新的一年 , 每个人都能迎着阳光、温暖前行!
一年即将过去 , 自然有各种重要事件的回顾和总结在媒体上涌现 , 它们浓缩了一年的图景 , 提示我们立足于什么样的时空 , 走过了怎样的日子 , 让我们产生与时代的共在感 。
然而 , 这种共在感并不能代替个体对时代的切己感知 。或许有人认为一些事在自己的感知之外发生 , 离自己如此遥远 , 以至于觉得自己被前行的列车遗弃在孤冷的小站;或许也有人认为一些事情之所以发生不过是因为大势所趋 , 只要顺应和认同便可心安理得 。诸如这般的感受 , 其实都透露了与时代相连接的缺失 。
我上大学的1980年 , 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情:旅行者1号飞掠土星 , 约翰·列侬被刺身亡 , 两伊战争爆发 , 索尼推出随身听 , 任天堂第一款游戏问世 , 罗兰·巴特去世 , 约翰·伯格《观看之道》出版……但是 , 当年我对这些一无所知 。直到后来 , 我在工作、阅读和日常生活中才逐渐与这些事件发生联系 , 这些事件对我的意义才慢慢清晰起来 。可以说 , 信息的缺失和我的后知后觉 , 延迟了我与时代的具体连接 。
在资讯发达的今天 , 不会有人如我当年那么迟钝;但能够迅速获知丰富的信息 , 个体与信息所标识的时代之间如何关联 , 就变得更加迫切而需要及时的追问 。如果没有这样的追问 , 哪怕我们拥有数据库般的信息 , 也有可能被其淹没和窒息;如果没有这样的追问 , 即便我们紧追所有的热点 , 也有可能感到与时代脱节 。
在最基本的层面 , 我们的追问是对自我在信息环境中真实存在的审视:是否将违心之举冠之以顺应潮流?是否将懈怠之心推诿给“躺平”大势?是否将注意力分散归因于移动互联网的无孔不入?是否将不择手段的竞争归因于无处不在的“内卷”?面对最流行的词语、最风靡的时尚、最爆款的网文、最吸睛的网红和最火爆的热点 , 是否能够保持基本的理性而不屈从于多巴胺的释放?在追逐各种新技术神话和预言中 , 我们是否既丧失了基本的历史感 , 又无视身处的现实?在围绕诸如元宇宙形成的各种叙事和言论中 , 我们是否能够辨明自主性焦虑的弥散和多种声音的交战?
追问须诉诸思考 。美国学者彼得斯的《奇云》去年底有了中译本 , 今年被新闻传播学界热读 。作者在书中提醒我们:“1964 年是一个人类思考技术、文化和社会的好年头 。”他列举了这一年出版的一系列重要著作 , 尤其强调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和古尔汉的《手势与言语》对于我们的意义 。前者视技术为人体器官的延伸 , 后者将人体器官视为技术的延伸 , 它们相互映照 , 洞见了技术与人的关系 。
但是 , 对同在这一年出版并风靡全球的《单向度的人》 , 彼得斯止于提及而未详述 。马尔库塞的这部著作关于技术理性和技术神话的论述 , 在今天也仍然具有启示性价值 。忽略《单向度的人》 , 与《奇云》的写作定位、思想关切和价值取向有关 。这样的忽略也意味着给不同的思考者留下了开放的空间 , 意味着对任何思想、任何事件的思考都有丰富的可能性 。农民工陈直研读海德格尔 , 透露出的也正是这种思考的力量和可能性的魅力 。当我们开始追寻更多的可能性 , 便是我们与时代发生具体连接的时刻 。
追问和思考 , 并非只是在抽象的层面展开 , 而总是与个体生命在特定情境中的鲜活感受相连 。几天前 , 我又一次造访曲园 , 走在马医科巷那条石子、石板和水泥混杂的窄路上 , 脚下发出不同的声响 。巷子里吹着冷冷的风 , 脑子里盘旋的却是“春在” 。三十岁那年 , 俞樾因为一句“花落春仍在” , 得到考官曾国藩激赏 。但他并非从此一路通达 , 而是在短暂辉煌之后迎来20余年的颠沛流离 。当俞樾筑曲园而定居 , 将最为轩敞明亮的厅堂命名为“春在堂”时 , 我想 , 他是在感念伯乐 , 纪念青春 , 也是在感慨自己历经人生的凛冬 , 却不曾放弃的希望和信念——那心中永远的“春在” 。这样的生命感受一定伴随着对学术真谛的求索与思考 , 最终凝聚于五百余卷的《春在堂全书》 。“春在”激发的所有解释、猜想、想象、移情 , 无不将后来者的体认与共情融汇其中 , 那是“花落春仍在”催化与生成的意义 , 也表明原本属于俞樾个体的关键词接通了更为广阔而深远的时空 。
- 拼多多自己的评论记录在哪(拼多多自己评论过的内容查询步骤)
- 四季物语属于什么类型游戏(四季物语游戏玩法说明)
- 原神寻找船上运送的东西任务怎么做(原神寻找船上运送的东西任务完成流程一览)
- 人们常说“五福临门”,下列哪个属于“五福”含意之一(蚂蚁庄园6月11日答案最新大全)
- 微信绑定的一码通不是自己的怎么改(微信不是本人绑定一码通更改方法详解)
- 寻找新业务方向 佳能将开发自动驾驶用摄像头
- 2022光遇1.15季节蜡烛在什么地方(光遇1.15季节蜡烛寻找位置分享)
- 原神|原神利用神之眼寻找碎星铁矿位置攻略一览
- 抖音里自己的评论去哪看(抖音自己的作品记录查询方法讲解)
- 王者荣耀营地创作菌的武器怎么找(王者荣耀营地创作菌的武器寻找位置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