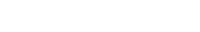以行为质变理论指引检察监督智能化( 三 )
以上并不是检察监督智能化发展的完整图景 , 检察机关应不断细化业务类型与行为类型 , 实现全方面、更小颗粒的行为监督 。智能治理方法的本质是模型治理 , 而非模式治理 。模型治理是在行为模式下采取更小的行为颗粒度进行监督与规制 。
智能治理是技术行为的升维和法律规范的降维 , 是技术与法律在行为层面的统一 。行为模型则是行为与规范的交叉产物 , 其兼具模式与规范的双重功能 。基于行为模型的治理 , 不仅可以做到更为精细的行为治理 , 还可以实现更为前置的行为治理;不仅可以实现更为弹性的行为治理 , 而且具有更高的行动效率 。
(二)大数据建模的方法理论突破 。如前所述 , 不同的业务场景和业务目的 , 需要采取不同的技术建模方法 。因而 , 能否突破之前的建模方法并形成大数据建模的方法理论体系 , 是实现监督智能化的最后一道关卡 。
大数据建模的方法本质就是要在庞大冗杂的大数据中挖掘出价值集中的有用信息 。在输入大数据后 , 系统根据大数据模型的算法处理 , 输出具有某种集中价值的分析结论 。大数据的分析结论一般是一个具有增值价值的小结论 。而大数据运用能否输出有用结论则取决于计算模型的有效构建 , 简称“大数据建模” 。
目前 , 实践中大数据建模主要有两大类型 , 即统计建模与行为建模 。统计建模是大数据行业普遍采用的、以统计方法为基础的建模方法 , 它们倾向于自然科学的建模方法 。行为建模是基于行为特征信息的大数据建模方法 , 主要运用于犯罪侦查、司法证明领域 , 主要有犯罪学行为建模方法和侦查学行为建模方法 , 它们倾向于社会科学的建模方法 。作为中立的技术方法 , 统计建模与行为建模本身并无泾渭之分 , 但这两类建模方法有各自的技术功能和概率特性 。一般来说 , 统计建模倾向于“发现问题所在” , 而行为建模倾向于“判断因果关系” 。
鉴于个案的特殊性 , 行为特征信息的提取往往与个案行为方式及其所涉及的网络信息系统直接相关 。因而 , 大数据的行为建模是一种具有个案针对性的具体技术方法 。大量的个案组成了类案或类型行为 , 所以 , 行为建模在类案或类型行为的调查或监督中也具有很强的推广效益 。通常 , 我们可以根据个案调查而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特征来构建类案或类型行为的算法模型 , 以此形成基于实时计算的智能监管体系 。
统计建模的相关关系与行为建模的因果关系二者其实是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从整体到部分的过程 。从大数据助力监督的角度看 , 统计建模通常在发现潜在问题行为上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 而行为建模则在行为的因果关系判断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检察监督智能化建设通常需要同时运用统计建模与行为建模 。
(三)行为基础数据的采集与共享 。目前包括检察智能监督在内的智能社会治理在实践层面很难推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数据的采集与共享问题 。其根源 , 一方面是人们认为大数据运用必然涉及隐私权等相关权利;另一方面是缺乏技术创新的能动性 。
大数据运用并非必然侵犯隐私权 , 这取决于数据行为与行为数据的法律属性 。如果某些行为本身属于监督(管)者的权力范围 , 那么该类行为所产生的数据记录则亦属于监督者有权收集分析的范围 , 即监督范围 。
检察监督智能化应摒弃“先达成数据共享共识”或者“先达成数据标准统一”的幻想 。技术带来的问题应当首先寻求技术方法来解决 , 而非诉诸管理或规范 , 虽然就长远而言 , 应尽可能使之如此 。从河北雄安新区的智能监督探索经验来看 , 边缘计算或加密计算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数据共享问题 , 其逻辑是:不需要拿到用户数据 , 但需要算法模型的计算结果 , 并通过边缘计算的技术方法反馈回来;如果担心数据泄露风险 , 则可以通过加密传输和加密计算来解决 。通过这种技术方案的设计 , 既不违背数据权利的归属 , 又能达到智能治理的共治 。而既有各种业务应用系统平台的数据采集不足问题 , 则一般可以通过插件改造来解决 。在技术自由的时代 , 办法总比困难多 。这正是信息时代的魅力所在 , 也是法律监督智能化发展所必须面对的创新挑战 。
- 支付宝蚂蚁庄园2022年6月27日答案更新(以下哪种热带水果除了果肉好吃,果核也是美味?6月27日答案分享)
- 我国四成以上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世界第一(新数据 新看点)
- 支付宝蚂蚁庄园2022年6月26日答案更新(运动健身后,喝以下哪种饮品更合适?6月26日答案分享)
- 快手打击欺骗诱导行为,处置重点违规账号347个
- 研究揭示镁金属负极的不均匀溶出行为
- 厉害了!液态金属也可以有磁性 中国科学家最新成果
- 洞头备案非标电动自行车集中淘汰置换:最高可补贴千元以上
- 亲情or恐怖:Alexa可以模仿故去亲人声音
- BrainCo 强脑科技韩璧丞获评《财富》“中国40位40岁以下的商界精英”
- 生死狙击2|《生死狙击2》官宣代言人周杰伦!公测定档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