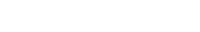阿基:艰难时世中的薄暮之光( 三 )
真喜欢阿基电影中的餐厅戏 。不为美食——这你想都别想 , 只为这里的众生 。当初 , 我也是看《希望的另一面》时 , 看那个收留了叙利亚难民的餐厅转而变成日料店 , 毫无防备给整得一顿爆笑 。镜头前一秒钟 , 厨师还在恶补日料菜谱 , 再一转 , 几个高大威猛的芬兰服务员、厨师再加领班 , 就一水儿的和服 , 开门迎客 。高大的北欧人站成一排的尬姿 , 真让人乐不可支 。又实在是理解 , 他们就是生活给逼的:没法儿整啊 。
没有多余的故事线 , 不做人物的情绪抒发 , 阿基的电影 , 却有这些冷幽默 , 实现着某种银幕上下的交汇流动 。当然 , 他还有另一个长项 , 就是音乐 。《希望的另一面》最开始让我动容 , 就是有一首幽幽地唱给母亲的歌 。《火柴厂女工》《浮生世事》不止一处用了老柴的《悲怆》 , 前者是青春生命的哀悼 , 后者是逝去平静生活的祭典 。都是阿基人物的心曲 , 它们让银幕画面变得潮润 , 也唤起你对很多经典电影的回忆 。
而我联想最多的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那几部 。那种电影史上的穷人的电影 , 早期的“无产阶级三部曲”(抑或叫“蓝领三部曲”)是 , 后面的《希望的另一面》等也是 。同样的悲悯 , 只是泪笑冷热之别 。意大利电影 , 有一种声响的世界 , 是由人物开口说话的腔调起伏构成 。拖长了如波浪般无限推展 , 短促密集了又有如小鸟叽喳般琐碎 。德·西卡《偷自行车的人》中就有一幕:父子俩为丢失的车四处奔走 , 急得跟什么似的 。偏偏逢雨 , 便躲在路边屋檐下 。那里也站着一堆神学院学生 , 你一言我一语 , 剧本上描述“他们像一群白嘴鸦似的叽里呱啦地吵个没完” 。越是如此 , 越衬出父子俩焦虑、落寞 。待到偷自行车的行为被发现 , 父子一起穿过人群 , 儿子终于牵起大人的手 , 你在此刻不落泪都难 。而回到阿基人物情境 , 他们悲催处固然有音乐起 , 但绝不会有这些旁衬 。电影卡到他们的身形 , 就像荒野中一棵孤木 , 醉酒到家的姿势都像 , 都是不打弯的直接扑地 , 而第二天爬起 , 生活继续 。
在阿基之前 , 你在银幕上见到的属于穷人的悲喜柔肠 , 多还是有出口宣泄映衬的那种 。到了阿基 , 则决然是另一种 。芬兰人是不是禀性都这样 , 没有接触没有发言权 。但是 , 重要的是 , 这样的芬兰人通过阿基的电影被我们看到 , 也仿佛看到疫情流调报告中最辛苦的那些人 。
“我不需要怜悯 , 树木照样生长 。”阿基电影中男主角看似笨拙的“卡” , 那种漠然的隐而不发 , 有这种冷然傲骨 , 但从另一方面 , 将生存意志从身体与灵魂中再次“拨”出来 , 他们也需要这种缓慢来做力量积蓄 。
- 13岁黄多多太艰难,染发遭吐槽不说,如今穿背心也遭到了“舆论”
- 《青春》:人生艰难的就是告别,人生不擅长的就是失去
- 杜新枝直播,熊磊发文称云昊说谎,北海舅妈改名,许敏处境变艰难
- “反诈老陈”辞职创业艰难,花钱拍摄视频遭限制,被嘉年华拖下水
- 文化新观察||J.K.罗琳另起炉灶不易,回归更加艰难
- 《浪姐》路透王心凌状态引热议,嘟嘴撒娇都艰难,曾多次否认动脸
- 观众起早贪黑看《狙击手》,票房艰难困苦破亿,你看了该片吗?
- 《相逢时节》剧情再掀高潮 雷佳音袁泉面对家庭恩怨艰难抉择
- TVB视帝停工后生活艰难,被拖欠百万工资,孩子一年学费就6位数
- 对话《人世间》编剧王海鸰:这是我从业以来最艰难的一次创作